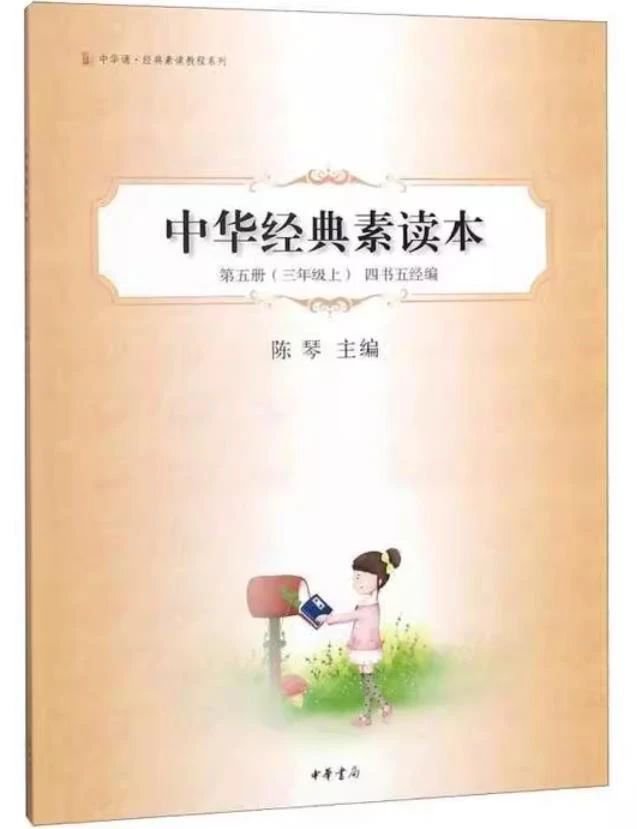2500多年前,孔夫子想移居九夷,也想过“乘桴浮于海”,然而终究不可行。他还是秉持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恒毅原则,一生不是求学,就是为政;不是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就是在编修“六经”教导弟子的事中。夫子已去,但夫子留下的经典成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之光最明亮的那部分,指引着我们走出黑暗的包裹。然而100多年前的晚清民初教育变革之际,小学读经科被废除,大学经学科被废止,随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要打倒孔家店。于是,夫子整理的“五经”和朱子编著的“四书”就逐步从我们的教育必修课程中消失了。

“五经”书影
我从2001年毕业20多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华经典教育的出版、教学和研究工作,其实就是想试着提出并解答一个问题:夫子经典,能否在未来的中国教育中适度归来?对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辈、前辈学者的理论思考与教育实践都浓缩在我的《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这部小书里。一部小书,见证了将自己微小的个体生命投入到经典传承发展事业中的点点滴滴,验证了将自己美好的岁月年华与践行经典传承发展事业相伴随的方方面面,更历史地记录了先辈们为经典传承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是一本磨砺我身心的著作,它自然而真实地在我的精神和肉体生命中一点一点挨过,不由得我不絮叨絮叨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2023年3月,拙作出版,我犹如完成了一件早该做但又似乎不该做的事。这看似矛盾的话,其实是情感与理性背离的结果:从编辑的身份属性上我不该写,但从责任理性的角度我必须出。我本是一个编书出身的人,无论是大众出版、学术出版还是教育出版的编辑,理论书籍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找合适的作者来写,课程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找合适的专家学者来讲,教材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找合适的编者来编,可是我在编辑岗位工作了近20年的时候非常突兀地放下编辑工作,转身走入教学科研岗位,并在3年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推出了这本拙作,实在是与长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岗位职责相违背。然而,我必须写出这本小书,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对我个人和很多同辈20多年经典教育思索和实践有一个交代,也才能告慰120多年以来前辈们的思考和实践。虽然个人才疏学浅,所见所思所行非常有限,但还是要做,那只能剩下两个字——死磕。
我在《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的《后记》中说“本书文字稿的完成,历时五载(2017—2022年)”,绝非虚言。其实从构思到撰写到修改再到推倒重来,直至渐入撰写正途,前前后后远超5年。
这部书稿的最初草稿在2019年5月2日就已经完成,为此我还在北京市房山区修德谷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经典教育分享会。当时有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和教师,牺牲“五一”小长假,齐聚交通不便的修德谷。这不是因为这个以我为主的经典教育分享会有多重要,而是大家对我从出版社走向高校科研岗位的暗自期许和祝福。
或许让他们很失望,因为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做,几乎放弃了本书的写作。所以,草稿虽早已完成,但是定稿遥遥无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和日常生活琐事所扰。人一旦踏入社会,就会有做不完的事。教学备课、撰写论文、申报课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恐慌,诸多琐屑困扰着书稿的修订。当然,更大的阻碍是来自本书各项准备工作的不完善,如相关文献整理不充分、案例收集不丰富、理论思考不深入等,这使我的书稿修订工作时时陷入停顿状态。直到2022年4月9日,书稿的修订才得以正式启动。那年3月中旬,我被隔离在了深圳市福田区的家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孤家寡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肯定孤寂与难过;而对于一个正在写作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啊。现在回想一下,要不是有那么一个多月的完全封闭时间,这部书稿能否出来,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撰稿过程的“死磕”还可以从不断变换的书名中看出,这部书稿2016年开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随想七则》为题结集,但那时我正带着20多人的团队死磕经典教材的编写与推广及经典教师的培训,根本没有时间来认真推敲书名。直到本书即将付梓时,书名都未能固定,先后考虑过的书名就有“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究十二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初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华经典教育初探”等。大概在2022年初,我将书名更改为“中华经典教育述论”,顾名思义,这就是一本有叙述有论述的关于中华经典教育的著作。但后来有前辈建议将书名更改为“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我也比较认可,在跟出版社编辑部负责人一番沟通后,才确定了这个名字。其实这本书涵盖的时间是从1900年到2021年,可以命名为“中华经典教育百年”,但因为内容大半还是集中在最近30年,所以目前这个命名还是最合适的。
这部书稿,从“种子”到开花结果,过程很是漫长,漫长到我用最宝贵的20多年生命时光就做这一件事情。所谓很漫长,既是很偶然的时间煎熬,又似乎是一段必然要经历的酝酿时光。
这部书稿的种子在20年前(200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已经种下。我的专业是思想史,我的导师胡伟希先生是冯契先生的博士,他对哲学史尤其是严复很有研究。在我研二时,胡老师大约暗示过我,学位论文可以以严复为主题,那一刻我也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毕竟严复先生是近代思想文化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然而,年轻人的叛逆心理最终占了上风,学位论文想自设题目。一次偶然听到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某位老师说,有一套《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丛书不错,从中可以挖掘多个博士生课题。于是我就去清华大学老图书馆找这套书,很可惜只找到了一册,一翻之下果然很好,又去地摊上买到了另外一本,虽然不完整,但关于1900年晚清教育改革前后的学制史料和思想史料还是有的。这时,正值饶宗颐先生倡导的“新经学”研究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方兴未艾之时,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说了一句话,蔡元培先生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时要独断地废除小学读经?我也是一愣,蔡先生不是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为什么对中华经典这么决绝呢?是不是有点独断?问题一旦产生,年轻的心就放不下了,于是就自己去查研究成果、收集资料,还像模像样地开题了,而这一切居然得到了导师胡伟希先生的默许。今天看到这本书,我不能不感谢导师对我学位论文选题的“放纵”。后来论文也艰难完成,胡老师还邀请了欧阳哲生、葛兆光、彭林、刘晓峰诸位先生莅临我的论文答辩会,我的《清末新政经学课程演变之研究》居然还得到了诸位先生的初步肯定,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心生感激。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实业教育 师范教育》书影
可惜的是,我硕士毕业后没有去读博,而是带着一颗要践行思想力量的躁动的心到出版社工作了。在编辑室最初的不到半年时间中,我先后在出版社的总编室、发行部、教材推广中心、市场部等部门不断“流浪”。其结果就是,读研期间积累的那一点思想灵光,被现实的工作消磨殆尽。好在2002年在做图书销售期间,硬是挤出时间从硕士学位论文中整理出一篇论文,投到王钧林先生主编的《孔子研究》,竟然刊发了,还收到一笔在当时看来绝对不菲的稿酬。于是,装了一回大款,邀请发行部的同事下馆子搓了一顿。或许这就是为后来写书做的准备工作,只不过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意义,只是觉得只有如此,才能对毕业论文有一个交代。
工作可以折磨人,但也可以成就人。今天这本书的出版,与我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2006年10月到2009年4月,我参与了《于丹〈论语〉心得》的图书出版工作。我曾在本书《后记》中写道:“感谢中华书局的李岩、徐俊、顾青等前辈和于丹教授,让我参与了《于丹〈论语〉心得》系列图书的营销工作,使我在与海内外大量读者的三四年交往中,亲身体验到作为经典的《论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诚哉斯言!如果从我的工作中截去这一特殊经历,此书能否问世,我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节目在2006年国庆黄金周的播出和《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我得以在该书销售最高峰期间、日接收的400余封信件中体味到经典的力量,得以在与社会各界优秀分子、普通人的交流中体会到经典打开胸襟的兴奋,得以在不同的城市签售、讲座、座谈中直接感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喜爱……这一切的日日夜夜的真实感受,是课堂上无法传授的,是书本上无法阅读的,是研讨会上无法给予的,也是期刊论文和经典文本中无法获得的,这就是经典打开的力量。一旦经典被打开,就会穿越千年时光,链接古今人之心,激发火热的生命动力,我称之为“经典心得大法”。这一段难忘、难得、难能的宝贵工作经历,直接注定了我要写出这样一本书,似乎是一种宿命。
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感谢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后改名为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全体同事的倾力支持和紧密合作,十年艰辛探索,其中的甘苦,只有你我知道。”这句话,其实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我在完成“于丹教授系列图书”的出版工作之后,于2009年4月启动了一家直属中华书局的小国企——北京阳光润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中华书局内部称之为经典教育推广中心,后来改名为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其主要负责经典校本教材和地方教材的编辑出版、教材的教研服务、经典教育论坛的组织及骨干教师的培训等。在主管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的过程中,有三件事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一是2014年把我国台湾董金裕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改编成《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并将之推广至全国高中;二是2016年参加山东省中小学地方必修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编撰,并成功入选;三是2018年为中华书局成功申报到中宣部文化创意发展基金500万元的支持资金。在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一段难忘的创业经历。我和我的团队体验了种种创业的艰辛,也体会到了小小收获后的喜悦。我们虽然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也做了很多人没有想过也没有干过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与经典教育高度相关,这对于我今天写出这本小书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一线实践。没有这个水与火的考验,我可能无法体悟我要写的是什么。
我在本书的《后记》说:“感谢海内外师友们对我的包容和支持,包括钱逊、楼宇烈、牟钟鉴、余敦康、董金裕、郭文斌、黄玉峰、屈哨兵、王财贵、陶继新、李山、徐勇、程方平、吴安春、于建福、从春侠、容宏、孟庆瑜、易理玉、彭鹏、柳恩铭、吴颍慧、周信、陈琴、洪伟、谢庆、徐海元、许凤英、张拥军、李国鹏、林美娟等师友们。”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位师友,我都可以写出一大段文字来。与他们的交往,不断推动着我的经典教育工作。比如董金裕先生所主编教材的引入改编就是钱逊先生的牵线搭桥,后期的推广更是离不开钱先生的认可和鼓励,钱先生关于经典教育的鲜明态度也坚定了我要持续把经典教育这件事做下去的信念。又比如余敦康先生,余先生是当代易学泰斗,我在余先生的学生寇方墀老师引荐下见到了余先生,那时余先生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站立,只能坐着说话,当听说我在做经典教育的工作时,先生很是激昂地说:“你要举大旗做大事啊!”这对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鼓励。再比如陈琴老师,2010年七八月我主办了经典师资研修营,王崧舟老师参加了此次研修营。通过王崧舟老师,我认识了陶继新先生,陶先生又向我推荐了陈琴老师。一番辗转,我和陈琴老师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之后我就飞到广州天河区华南师大附小去见她,听她的课。记得我当时暂住在华南师大附小附近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酒店房间中,前后十来天,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听陈老师的课,去与她的学校领导沟通,去与她的同事沟通,去与她的学生沟通,去与她的学生家长沟通,甚至与她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沟通,了解经典素读的教学效果。正是在这样的深入了解下,我们团队配合陈琴老师,出版了《经典即人生:文字是修正灵魂的良药》和一部12卷本的《中华经典素读本》。就是在与这些师友的沟通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加深了对经典教育的认识,得到了坚持下去的鼓励,也收获了诸多的写作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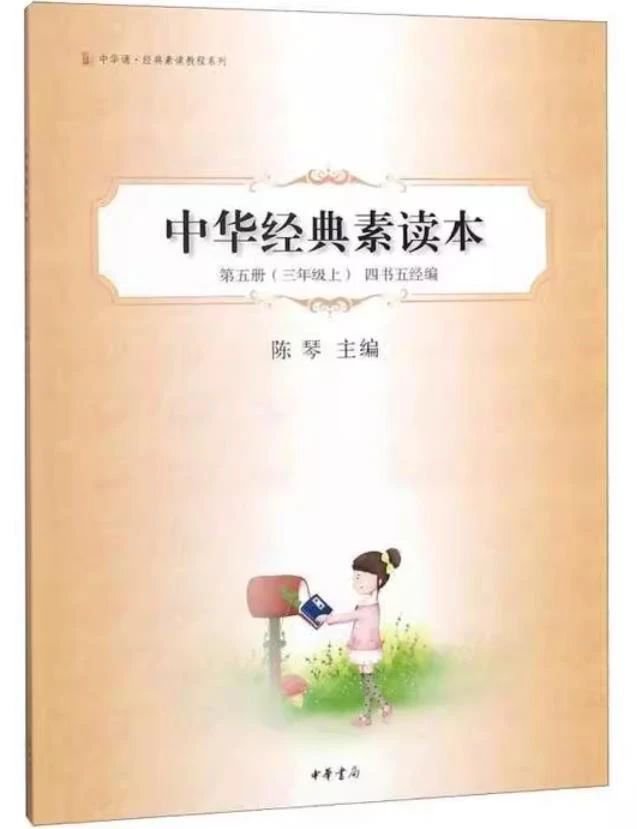 2019年5月我离开中华书局,入职深圳大学。这次工作调整,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转换,不如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2001年毕业时,我就特别想去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深圳工作。但对当时的我而言,火车票票价较贵,旅途又太过漫长,加之校招还不太流行,我就与深圳失之交臂。2006年到2008年之间,由于负责于丹教授的图书出版,我经常到深圳出差,对深圳有了一点了解,但由于来去匆匆,也没有直观的感受。直到2009年以后,我因经典教育结缘了深圳中学的一批老师,才对深圳有了直观感受。之后,我在获得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的认可后,在友人的协助下,加入到了深圳大学的大家庭中。
从出版行业转职教学科研,要面对的困难很多,我暗自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断绝了我跟学生和大学同事之间的直接联系,不能入校、不能参加学术研讨、不能去听想听的课……在这种隔绝的环境中,我的心灵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繁杂而获得了安宁,可以专心投入到书稿的修订中。在这种少有的安静气氛中,我的写作思路越来越清晰,最终完成了全部书稿的修订。可以说,在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3年宝贵的时间里,这部《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的书稿是其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工作;后来又在广州大学以屈哨兵书记为首的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我的这部书稿被纳入到其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司的重大课题中,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部书的决心。
这本小书可谓“生不逢时”,不仅没有赶上时代热点,还被时代热点所冲淡,但由于满满的问题意识,反而使这本书不应景却值得翻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蒙学热、汉字热、中医热、经典热、国学热等文化热潮迭兴,在与西方文化热的相互纷争中,热点一直持续到2014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发展维度,不再忽冷忽热,此其一;其二就是世人的眼光逐渐被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等打断、分散和转移,所有的热点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都变得渺小。
同时,民间读经转入持续小规模深入发展阶段,不再是头脑发热式加入,也不再有很多的机构或个人一拥而入,而是存活下来不多的私塾和学堂慢慢地开始精耕细作,整体深化摸索读经教育的更好模式;各级各类学校的经典诵读、经典教育也进入健康发展状态,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少了,表演式的活动减少了,内涵式发展多了;一些企事业培训机构,由于线下活动的局限,开始转入线上活动。
经典教育经过30余年的持续发酵及各个参与方开始转向理性之后,这本小书出现了,它不会被热切关注,但也不失时机地对过去作了一些总结,作了一些分析,作了一些回顾,我想这个时机或许是合适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集成的反应。
这本书严格来说既不是经典教育史,也不是理论研究论文集。从实践角度而言,它是对如下几个重大问题给出的尝试性解答:中华经典教育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过去是怎么做的?现在又是怎么做的?将来要如何做?从课程理论上来说,中华经典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课程培养目标是什么?教学实施路径是什么?谁来实施?怎么评价?等等。
这本小书是对当下经典教育问题的尝试性解答,是对吴汝纶“西学未兴,吾学先亡”感叹的回答,是对张之洞从保全经典到存古学堂而不得之志业未酬的回答,是对蔡元培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大学经学科后续延伸问题的回答,是对以赵朴初先生为首的9位老先生《关于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回答,更是对当代学者洪明在《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中所说“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的回答。
我对经典教育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放到了一个时代大思潮的框架内思考。为此,我特地开辟了一章“中华经典教育的时代思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界先后兴起的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儒学教育、读经教育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潮作了分析比较。我认为,经典教育最终可以归纳为“人”的教育。在我看来,经典教育不过是人文学者在当代科技思潮占据主流的过程中,为人文教育争取其合理应有地位而掀起的人文学运动中的一部分。
中华经典教育是一个老问题,是一个100多年没有解决好的世纪难题,为了对这个百年难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我特别用三章的篇幅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发展、海外的历史发展、1991年以来经典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试图梳理清楚经典教育的发展历程、普遍经验和发展趋势,在把握了这个新趋势之后,再给出新的解决思路。所以我同样用三章的篇幅来阐述我的新思路,那就是“中华经典课程体系初探”、“中华经典课程教学方案”和“中华经典教材体系构建”。
其实,这本小书在与出版社编辑交流的过程中,编辑也是顾虑重重。除了拙作的可读性不强之外,编辑更对经典教育透露出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充满了担忧。但是我跟编辑说,我起码有新的思路,走出了过去对经典教育的认识范围,更为重要的,我的思考维度完全是为了未来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准备的,不是对历史的安慰,也不是对当下的指导,而是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世界和中国如何自存和如何共存而设计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我们要做的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叶澜语)的中国特色教育事业。
如果要说这本小书到底有什么创新,那就是本书《引言》所言:“经典蕴藏思维,经典教育训练思维方式。”“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来说,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中华民族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建构。”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通过经典教育的开展,训练民族思维方式,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养成君子理想人格。如果要从内容上来说,就是以《周易》、“四书”、“四大名著”、“4卷本《毛泽东选集》”等13部经典著作搭建,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打通的内容框架。
与安顺先生认识多年,早些年他以中华书局为依托,做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出版和推广,足迹遍布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典诵读之声也随着他的努力,在不少地方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笔者曾参与过安顺先生和他年轻同事们举办的经典教育活动,深受感动。
安顺先生不单是行动者,也是经典教育理论的思考者。他出身于清华大学思想史专业,有这方面思考的能力和才学。有句笑话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安顺先生思考经典教育的理论,却是由自身实践而来。
经典教育的兴起,其前导是发乎民间的“国学热”。相伴而来的各种关于“国学”的教育价值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歪理”也不少。安顺先生的书,不取“国学”这个叫法,而取“经典教育”,很好。
……经典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与思考,安顺先生的书就是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成果。不能说他的书是“孤明先发”,但说他的思考处在经典教育方阵的靠前位置,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而黄玉峰先生在《跋》中所言,更是让我惶恐不安,我根本不敢承受老师的赞誉,所以我在微信公众号上说:“这篇文字,黄师写得时间早,写得好,写得意义重大,但我还是放到了书的后面。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黄师的文笔太好,尤其是过高表扬了一个小编辑,实在不敢当!但整篇文字,黄师的鼓励和爱护后进之心跃然纸上,我只把它当作我不敢停歇的动力。”
一本小书真能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却耗尽了我的心力。对我个人来说,应该可以画一个句号,但现在想来,可能只是开启了一个冒号,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很多的书要编、很多的课要设计。如果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如果还有一些同志一起前行,如果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我将继续努力以告慰夫子:2500年后,有一批后学,在做一点点努力,希望使夫子的经典乘着经典教育的车驾,适度回归!
2019年5月我离开中华书局,入职深圳大学。这次工作调整,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转换,不如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2001年毕业时,我就特别想去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深圳工作。但对当时的我而言,火车票票价较贵,旅途又太过漫长,加之校招还不太流行,我就与深圳失之交臂。2006年到2008年之间,由于负责于丹教授的图书出版,我经常到深圳出差,对深圳有了一点了解,但由于来去匆匆,也没有直观的感受。直到2009年以后,我因经典教育结缘了深圳中学的一批老师,才对深圳有了直观感受。之后,我在获得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的认可后,在友人的协助下,加入到了深圳大学的大家庭中。
从出版行业转职教学科研,要面对的困难很多,我暗自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断绝了我跟学生和大学同事之间的直接联系,不能入校、不能参加学术研讨、不能去听想听的课……在这种隔绝的环境中,我的心灵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繁杂而获得了安宁,可以专心投入到书稿的修订中。在这种少有的安静气氛中,我的写作思路越来越清晰,最终完成了全部书稿的修订。可以说,在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3年宝贵的时间里,这部《中华经典教育三十年》的书稿是其中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工作;后来又在广州大学以屈哨兵书记为首的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我的这部书稿被纳入到其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司的重大课题中,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部书的决心。
这本小书可谓“生不逢时”,不仅没有赶上时代热点,还被时代热点所冲淡,但由于满满的问题意识,反而使这本书不应景却值得翻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上,蒙学热、汉字热、中医热、经典热、国学热等文化热潮迭兴,在与西方文化热的相互纷争中,热点一直持续到2014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发展维度,不再忽冷忽热,此其一;其二就是世人的眼光逐渐被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等打断、分散和转移,所有的热点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都变得渺小。
同时,民间读经转入持续小规模深入发展阶段,不再是头脑发热式加入,也不再有很多的机构或个人一拥而入,而是存活下来不多的私塾和学堂慢慢地开始精耕细作,整体深化摸索读经教育的更好模式;各级各类学校的经典诵读、经典教育也进入健康发展状态,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少了,表演式的活动减少了,内涵式发展多了;一些企事业培训机构,由于线下活动的局限,开始转入线上活动。
经典教育经过30余年的持续发酵及各个参与方开始转向理性之后,这本小书出现了,它不会被热切关注,但也不失时机地对过去作了一些总结,作了一些分析,作了一些回顾,我想这个时机或许是合适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集成的反应。
这本书严格来说既不是经典教育史,也不是理论研究论文集。从实践角度而言,它是对如下几个重大问题给出的尝试性解答:中华经典教育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过去是怎么做的?现在又是怎么做的?将来要如何做?从课程理论上来说,中华经典课程的目的是什么?课程培养目标是什么?教学实施路径是什么?谁来实施?怎么评价?等等。
这本小书是对当下经典教育问题的尝试性解答,是对吴汝纶“西学未兴,吾学先亡”感叹的回答,是对张之洞从保全经典到存古学堂而不得之志业未酬的回答,是对蔡元培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大学经学科后续延伸问题的回答,是对以赵朴初先生为首的9位老先生《关于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回答,更是对当代学者洪明在《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中所说“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的回答。
我对经典教育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放到了一个时代大思潮的框架内思考。为此,我特地开辟了一章“中华经典教育的时代思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界先后兴起的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儒学教育、读经教育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潮作了分析比较。我认为,经典教育最终可以归纳为“人”的教育。在我看来,经典教育不过是人文学者在当代科技思潮占据主流的过程中,为人文教育争取其合理应有地位而掀起的人文学运动中的一部分。
中华经典教育是一个老问题,是一个100多年没有解决好的世纪难题,为了对这个百年难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我特别用三章的篇幅来分析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发展、海外的历史发展、1991年以来经典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试图梳理清楚经典教育的发展历程、普遍经验和发展趋势,在把握了这个新趋势之后,再给出新的解决思路。所以我同样用三章的篇幅来阐述我的新思路,那就是“中华经典课程体系初探”、“中华经典课程教学方案”和“中华经典教材体系构建”。
其实,这本小书在与出版社编辑交流的过程中,编辑也是顾虑重重。除了拙作的可读性不强之外,编辑更对经典教育透露出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充满了担忧。但是我跟编辑说,我起码有新的思路,走出了过去对经典教育的认识范围,更为重要的,我的思考维度完全是为了未来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准备的,不是对历史的安慰,也不是对当下的指导,而是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世界和中国如何自存和如何共存而设计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我们要做的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叶澜语)的中国特色教育事业。
如果要说这本小书到底有什么创新,那就是本书《引言》所言:“经典蕴藏思维,经典教育训练思维方式。”“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来说,民族核心经典蕴藏着民族的思维本源、价值取向和意义世界。中华民族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建构。”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通过经典教育的开展,训练民族思维方式,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养成君子理想人格。如果要从内容上来说,就是以《周易》、“四书”、“四大名著”、“4卷本《毛泽东选集》”等13部经典著作搭建,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打通的内容框架。
与安顺先生认识多年,早些年他以中华书局为依托,做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出版和推广,足迹遍布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典诵读之声也随着他的努力,在不少地方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笔者曾参与过安顺先生和他年轻同事们举办的经典教育活动,深受感动。
安顺先生不单是行动者,也是经典教育理论的思考者。他出身于清华大学思想史专业,有这方面思考的能力和才学。有句笑话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安顺先生思考经典教育的理论,却是由自身实践而来。
经典教育的兴起,其前导是发乎民间的“国学热”。相伴而来的各种关于“国学”的教育价值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歪理”也不少。安顺先生的书,不取“国学”这个叫法,而取“经典教育”,很好。
……经典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与思考,安顺先生的书就是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成果。不能说他的书是“孤明先发”,但说他的思考处在经典教育方阵的靠前位置,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而黄玉峰先生在《跋》中所言,更是让我惶恐不安,我根本不敢承受老师的赞誉,所以我在微信公众号上说:“这篇文字,黄师写得时间早,写得好,写得意义重大,但我还是放到了书的后面。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黄师的文笔太好,尤其是过高表扬了一个小编辑,实在不敢当!但整篇文字,黄师的鼓励和爱护后进之心跃然纸上,我只把它当作我不敢停歇的动力。”
一本小书真能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却耗尽了我的心力。对我个人来说,应该可以画一个句号,但现在想来,可能只是开启了一个冒号,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很多的书要编、很多的课要设计。如果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如果还有一些同志一起前行,如果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我将继续努力以告慰夫子:2500年后,有一批后学,在做一点点努力,希望使夫子的经典乘着经典教育的车驾,适度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