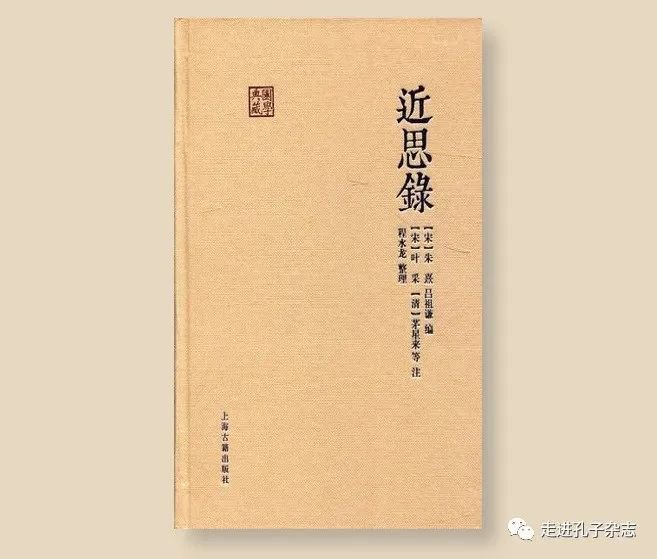文化本身是有生命的。一部文化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举世罕见,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我们的古圣先贤能够洞察天道、世务与人心,彰显为道德、事功与文章,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文化经典。这些经典,体现着民族精神世界的宽广、强大与深沉,她们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群,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又像大地上奔流不息的江河,长久地滋养着整个中华民族。
八百多年前,由南宋朱熹、吕祖谦两位大儒联手,从北宋“道学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著述中,选辑“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分类编纂而成的《近思录》一书,正是这些经典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国学大师钱穆曾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选出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近思录》即为其一(其余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传习录》)。他称赞这七部书为“新七经”,是中国思想史“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所在。钱先生这种选择,无疑偏重了“文化”诸领域中的“学术思想”方面,但无论如何,将《近思录》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可算指出了此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那么,《近思录》何以产生?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较之历史上的诸多典籍,包括钱先生提及的其他六本名著,其内容与特色何在?于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近思录》系列”要逐一探讨的问题。
朱子、吕祖谦为何要编辑《近思录》这样一部书呢?根据朱子在“序言”中的说法: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到访他所在福建建阳的寒泉精舍,留居了十余天(按,此乃朱、吕等人前赴江西信州鹅湖寺参与江西陆九渊兄弟“鹅湖之会”的前夕),两人共读周、张、二程之书,感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崖”,担心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故选取书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以期“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朱子还告诫说:学者熟读此书后,更应“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真正窥见四子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走一条深造自得之路,“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苦心美意。即此可见,朱、吕对《近思录》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引领学者迈入北宋“四子”思想殿堂的入门书。
朱子的这种说法,还只能算一个直接、表层的说明。两人汇编《近思录》,更深的意图是要辟邪显正,救治陷溺的时代人心,引导学者走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圣道路。不须说,作为伊洛道学的嫡系传人,朱子对周、张、二程的学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四子”的出现,使得孟子之后中辍千年的儒道焕然复明,后人只有读他们的书,才更容易窥得圣学之堂奥。朱子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里的“四子”,是指“四书”,意为“四书”是进入“六经”的阶梯,《近思录》又是进入“四书”的阶梯。朱子此言,与程颐对他的影响有关。“河南程夫子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朱子自己对“四书”的领会,也正是以二程(当然也包括二程后学)为“阶梯”的,这在他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已显露无疑。
《近思录》成为“四书”之阶梯,不仅在于四子“复明”了“圣道”,还在于它具有直指人心的鲜明时代性。朱子说:“《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书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切问而近思”。所谓“近思”,即要人切近自己的身心思量,不必舍近求远。至于他说的“人病”,除了学者的个人问题外,更与当时流行的学问有关,这既包括陷溺人心的功利之学,也包括无关身心性命的训诂、词章之学,当然还有他批判的,以荆公新学、佛老之学为代表的“异端邪说”。即此而论,《近思录》更是一部收拾人心、拨乱反正的弘道之书。
编纂《近思录》的实际过程,完全不像朱子“序言”中说得那样轻松,即朱、吕在寒泉精舍中“留止旬日”的结果,二人别后又会晤磋商,多次书来信往,为书中条目的编排择取可谓殚精竭虑(张载的言论就是在后期补入的),这种状况一直到吕氏的辞世。朱子尤多尽其增补删修之劳,前后经历十三年,才形成今天的文本面目。从《朱子语类》的记述看,《近思录》称得上是朱子晚年教导学生的课本,《语类》的很多问答,都是围绕书中的条目展开的。不难想见,此书的编辑刊布,大大促进了伊洛道学的传播。相比之下,当时的其他一些儒家学派,由于无人(尤其缺乏朱、陆这样有影响力的大学者)从事如此用心的编纂工作,就缺乏一部凝聚人心的传习经典,对本学派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性著作,《近思录》共选录周、张、二程的言论 622 条(其中邵雍的一条,由程颢之口说出),分为14卷,内容涉及天道、性命、为学、存养、政治等方面。这一编纂体例,本身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为后来的儒家“教材”建立了规模体例,几乎可以说,明代朝廷编修的《性理大全》等科举用书,不过是此书的扩展版。

朱熹画像
著名注家、朱子的再传弟子叶采,称赞《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依朱子之序,书的内容包括“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后来的编注者根据《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给每卷添加了“道体”“为学”等题目,这些题目在文字上略有出入,意思则大同小异,都起到了显豁题旨的作用。书的内容编排,明显受到《大学》“三纲八目”思路的影响。清代注家茅星来说:“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近思录集注序》)具体来说,卷二“为学”大体上相当于《大学》篇首的“三纲领”;卷三“致知”、卷四“存养”相当于《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卷五“治己”、卷六“家道”、卷七“出处”相当于《大学》的“修身、齐家”;后面的卷八“治体”、卷九“治法”、卷一〇“政事”、卷一一“治人”、卷一二“警戒”,则相当于《大学》的“治国平天下”。以上十一卷是全书的主体,构成了一整套“格治诚正修齐治平”的工夫系统。至于最后的卷一三“异端之学”与卷一四“圣贤气象”,可算是一种补充,一辨明“异端之学”的危害,一揭示儒家圣贤的精神气度,两卷与全书倡明圣学的旨归也是一致的。
书中最特殊的,还是最前面的“道体”一卷,它类似于今人著作的“前言”,通篇在讲“天道”“性命”之类的抽象义理。叶采说,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但他以为此卷即朱子所谓的“求端”,窃以为未必准确。相比之下,卷二谈“为学大要”,标举“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诸论,才更像“求端”。与其他各卷相比,“道体”卷显得太过深奥,有违“近思”“切于日用”的初衷。朱子后来说,他最初并不想设立这一卷,是吕祖谦的建议如此,自己也“觉得无头,只得存之”。“无头”,即缺乏一个纲领性“绪论”。吕祖谦的理由是:“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近思录后引》)意思是说:这类深奥的义理,虽不宜骤然对年轻人谈论太多,但读者若对此一无所知,就不明白整个儒学的义理梗概,也缺乏一个“向望”的探求目标,不如姑且置之于书前。
难懂归难懂,就结构看,“道体”卷无疑是《近思录》极重要的板块,凸显了它作为“性理之书”的特点。如所周知,儒家思想本脱胎于周代的王官之学,乃以“六经”“六艺”为基本内容,这是一种以政教伦常为核心的礼乐文化。“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所谈多是人伦日用。至于“性与天道”之论,《孟子》《中庸》中虽有一些,《易传》尤其多一些,但仍算不上原始儒学的重心,《近思录》则对此大谈特谈,从《太极图说》到《程氏易传》《张子正蒙》,可谓应有尽有。“道体”卷的文字篇幅,尽管不过全书的十分之一,但由于被放置在开篇,就占据了统摄性地位,同其余各卷构成一种“体”“用”关系,特别是与十四卷“观圣贤气象”前后呼应,一属于未发之“中”,一属于已发之“和”。一言以蔽之,“道体”卷的设立,弥补了传统儒家“本体论”的不足,解决了儒家修身实践的先天根据问题。
《近思录》的思想特色,不仅事关濂、洛、关、闽之学的异同分化,更关系到“道学”一脉与儒门内外各家各派的义理葛藤,这是本“系列”的论述重心所在,后文的几部分都与此紧密相关。比如“文公自是经纶手”一节,介绍朱子对《近思录》里里外外的笼罩性影响;“发明实推内圣功”一节,分析宋代理学由“外王”向“内圣”偏移的风力转向;“谁入佛老归六经”一节,探究北宋“四子”对佛老之学的“入室操戈”“修本以胜之”。至于对“成圣”问题的思想史讨论,乃是以先秦儒学、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宗等为参照,衡论《近思录》所代表的程朱理学工夫论之是是非非。诸如此类,为避免重复,这里不详细展开。
总体来说,《近思录》的问世,掀开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篇章,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开辟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新天地,体现了宋代道学家对古典儒学的创造性发展。究原其实,乃因为周、张、二程和朱子对“四书五经”之微言大义的寻绎诠释与深造自得,实际上是出新解于陈编,化学问为人格,大大地发展,乃至重构了儒家的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后来宋明理学(包括心学)如天命气质、天理人欲、未发已发之类的许多话头,字面上虽可遥溯先秦古典,实际上更多是以此为据点引申发展出来的。
如在“道体”卷,道学家为了给心性工夫寻找形上依据(也出于对抗佛、老的需要),几乎将先秦儒家典籍中有关天道性命的话题,诸如“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之类,尽数挑选出来加以发挥。其他各卷,虽未必直接谈心性的问题,也常会往这方面引申。《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章,究竟是孔子在感叹岁月匆迫,还是伤怀时事,后世已难确诂。但程颢解释说:“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慎独。”(《近思录》卷四)这就把孔子的“逝者”往“圣心”“天德”上引申,并与“慎独”工夫相结合。注家集解,也无不顺此思想脉络,如叶采引用朱子之言:“圣人见川流之不息,叹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体,惟圣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于此可见圣人‘纯亦不已’之心矣。”(《近思录集解》)这类创造性解释,未必合乎孔子本义,当时却自有深刻、合理的一面,足以让求道之人心向往之
以今人的眼光,宋儒对古典儒学的诠解,当然是“旧瓶装新酒”。但这又不是把瓶中的旧酒全部倒掉,另装一完全不同的酒,而是加入新的成分,使之成为一种适合时代风味的新酒。《近思录》有着“内圣外王”的义理规模,这是儒家的“旧瓶”。就“新酒” 而言,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通过静坐体悟的方式“学以成圣”,这无疑是对孔、孟修身之学的调适上遂,使得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性格愈发凸显。这一新成分的加入,也使《近思录》与“四书五经”相比,更像一部“谈修行”的书。之所以加入这一“新酒”,显然与佛、老二教的刺激与影响有关,倘不如此,时人就不爱喝,儒门就会继续“淡薄”,继续“收拾不住”。这种情形,正如在鸦片战争之后,倘若不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华民族就无法救亡图存一样。不同的是,与后者以坚船利炮的强烈冲击为特征不同,佛教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长期浸润,很多道学家本人对此也浑然不觉,他们自然也不会承认,自己对儒家道统的复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当然,这种“新酒”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问的翻新,又会变成人们不爱喝的“旧酒”,尤其是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思想而变得日益僵化和形式化之后,就有以《传习录》为经典的阳明心学这一“新酒”来代替它。而明亡之后,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遭到各种批判,极端者如清儒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
在朱子生前,《近思录》已刊刻流传,朱子也喜以此书赠人。朱子辞世后,随着其人其学名誉的恢复,此书更得到广泛认可,成为后世儒者的案头必备书。叶采称《近思录》为“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也”(《近思录集解序》)。四库馆臣誉之为“性理诸书之祖”。清末沈锡周说:“《近思录》一书,发明圣贤大义微言,如日中天,明彻无疑,四子、六经而外, 仅见此书。”(《五子近思录发明跋》)日本人高津泰说:“学者苟志圣贤之道,而欲穷洙泗之渊源者,舍此书而无他途也。”(《近思录训蒙辑疏序》)直到今人钱穆,犹言“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这些话很有代表性,但不过是《近思录》所受赞誉中的极少一部分。
《近思录》成书后,专门为之注解者就不下30人,著名者如宋人叶采,清人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其中叶采积三十年之力撰成的《近思录集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陈荣捷先生说:“《近思录》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近思录详注集评》)这是信实的论断。据程水龙教授考察,在朱子身后的八百年间,各类注释、续编、仿编等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至今国内存世的近200种,韩国现藏传本计有49种268部,日本现藏传本30多种近60部,且日本人注解、讲说的文本另有近50种(《〈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近思录》的传刻,不啻为东亚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此书在近世儒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藉此也可窥一斑。
一种思想传统的生命力,总是在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中展现出来的。魏晋南北朝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儒家在民众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不突出。作为传播和普及儒家知识的教科书,唐代编纂的《五经正义》与社会人生实践是脱节的。相比之下,反倒是佛、道二教更为深入人心,尤其是佛教禅宗长期代表着思想文化的“高明面”,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宋灭亡都没有彻底改观,南宋的孝宗,还亲自撰有宣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原道论》。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尽管只有到阳明心学的勃兴, 儒家的“内圣学”才达到了顶峰,但《近思录》问世与盛传,大抵可视为儒家与佛、老在思想疆场上长期争锋拉锯而取得关键性胜利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有了北宋“四子”,有了朱子这样一位手持《近思录》登场的儒家大宗师,儒学才真正战胜了佛老,重新成为民族精神的主调。
北宋“四子”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重塑,不管后世有怎样的褒贬酷评,都无法动摇这一铁的事实,即像本文的题目一样,“一部粹言经可传”,作为一部继往开来的书,《近思录》不仅是“四子之阶梯”,是接续古典儒学的津梁,同时是支撑儒家文化赓续发展的“新约”。如果说,古典儒学是要人做一个仁礼双彰、文质彬彬的君子;那么,宋明理学则要人做一个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圣人。即此而言,《近思录》适应了时代需求,凝聚了时代精神,在义理上跨越汉唐,远祧周孔,旁汲老庄、佛禅,下启朱子、阳明,俨然中国思想殿堂的一大洞藏,中国文化江河中的一大长川。欲了解中国民族在近800年来的精神流变,《近思录》是首屈一指的必读书。